余華兩個(gè)人的歷史解析?余華的《兄弟》講述了文革前后劉鎮(zhèn)一個(gè)四合院的故事,普通人和簡單的事物展現(xiàn)了文革時(shí)期的歷史場(chǎng)景,即歷史力量的存在和普通人的無奈與絕望。《兄弟》的上半部分主要講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故事。那么,余華兩個(gè)人的歷史解析?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讀過余華的人都會(huì)有這樣一種感覺:平凡的故事正在講述,說不定哪就會(huì)出現(xiàn)血腥、出現(xiàn)死亡、出現(xiàn)你絕對(duì)意想不到的悲慘情節(jié)。
如果說在他的短篇作品中出現(xiàn)這樣的冷酷筆調(diào),人們還能勉強(qiáng)接受,那么在一部長篇中,當(dāng)故事進(jìn)行到了最后,主人公離奇死亡,哪怕是順理成章,讀者似乎也是再怎么勉強(qiáng)也難以接受的。
比如《兄弟》這部長篇。
宋剛的慘死無疑是一個(gè)悲劇,這是每個(gè)讀者都能理解的,而李光頭的飛黃騰達(dá)呢?這,無疑也是一出悲劇。
兄弟二人性格迥異,導(dǎo)致了日后生活上的絕對(duì)反差,善良者為生活所迫,最終慘死,邪惡者偷奸取巧,竟成億萬富翁。
這樣的結(jié)局安排其實(shí)是很老套的,翻開明清,大凡以“反抗專制”為主題的悲歲滲滾劇作品,多以“良善者受欺、邪惡者發(fā)達(dá)”為終點(diǎn),目的很簡單:強(qiáng)化作品的悲劇色彩,加大作品的批判力度。
余華的《乎余兄弟》總體上走得也是這一套路,所不同的是,這樣一種思想的表達(dá),摻入了更多、更復(fù)雜的關(guān)系,倘若單以“批評(píng)”二字來加以概括,那么也未免太小看余華了。
無數(shù)的創(chuàng)作表明,真正能成為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作品,絕不會(huì)是“就事論事”“喊世有一說一”的。
如果《紅樓夢(mèng)》單是講兒女私情、家常里短,那么它是斷無傳世之可能的。
余華作品看似平淡,但卻內(nèi)含深刻,奉之以“微言大義”,似乎也未嘗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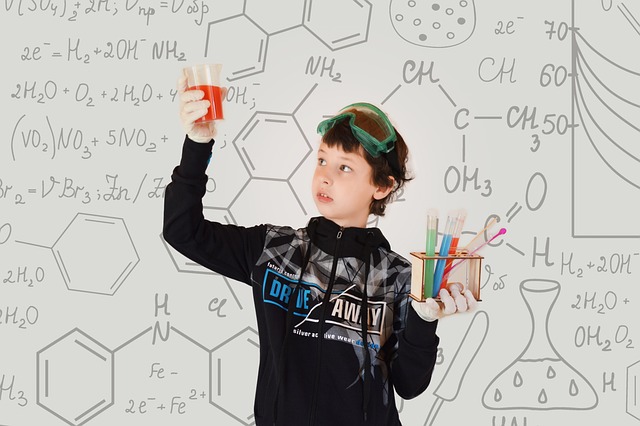
余華,浙江海鹽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來隨父母遷居海鹽縣。中學(xué)畢業(yè)后,因父母為醫(yī)生關(guān)系,余華曾當(dāng)過牙醫(yī),五年后棄醫(yī)從文,進(jìn)入縣文化館和嘉興文聯(lián),從此與創(chuàng)作結(jié)下不解之緣。余華曾在北京魯迅文學(xué)院與北師大中文系蘆衡漏合辦的研究生班深造。余華在1984年開始發(fā)表,是中國大陸先鋒派的代表人物,并與葉兆言和蘇童等人齊名。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陪爛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和日文等在國外出版。其中《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shí)入選百位批評(píng)家和文學(xué)編輯評(píng)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曾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xué)獎(jiǎng)(1998年),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xué)獎(jiǎng)(2002年)。 著有短篇集《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世事如煙》,攔液和長篇《活著》、《在細(xì)雨中呼喊》及《戰(zhàn)栗》。
P.S:我個(gè)人比較喜歡《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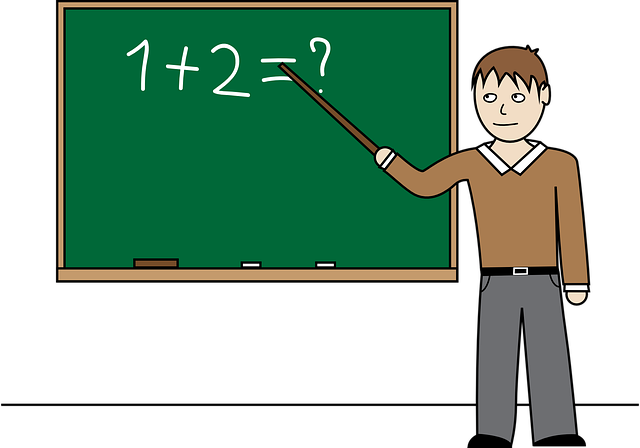
這本書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長度的迷戀,一條道路、一條河流、一條雨后的彩虹、一個(gè)綿延不絕的回憶、一首有始無終的民歌、一個(gè)人的一生。這一切猶如盤起來的一捆繩子,被敘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盡頭。
在這里,作者有時(shí)候會(huì)無所事事 因?yàn)樗麖囊婚_始就發(fā)現(xiàn)虛構(gòu)的人物同樣有自己的聲音,他認(rèn)為應(yīng)該尊重這些聲音,讓它們自己去風(fēng)中尋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敘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聽者,一位耐心、仔細(xì)、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聽者、他努力這樣去做,在敘述的時(shí)候,他試圖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覺得自己應(yīng)該是一位讀者。事實(shí)也是如此,當(dāng)這本書完成之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別人多。
歲侍書中的人物經(jīng)常自己開口說話,有時(shí)候會(huì)讓作者嚇一搜大跳,當(dāng)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話在虛構(gòu)的嘴里脫口而出時(shí),作者會(huì)突然自卑起來,心里暗想:“我可說不出這樣的話。”然而,當(dāng)他成為一位真正的讀者,當(dāng)他閱讀別人的作品時(shí),他又時(shí)常暗自得意:“我也說過這樣的話。”
這似乎就是文學(xué)的樂趣,我們需要它的影響,來糾正我們的思想和態(tài)度。有趣的是,當(dāng)眾多偉大的作品影響著一位作者時(shí),他會(huì)發(fā)現(xiàn)自己虛構(gòu)的人物也正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著他。
這本書其實(shí)是一首很長的民歌,它的節(jié)奏是回憶的速度,旋律溫和地跳躍著,休止符被韻腳隱藏了起來。
剛看過活著,有點(diǎn)小感受,如下:
1.《活著》描寫了時(shí)代壓在人肩上的苦難,這些弊清苦難深重而難以承受。主人公的種種期望,都被現(xiàn)實(shí)無情的埋葬,所以相對(duì)于“活著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 這句話之外的是指 “為了希望或者意義而活著”,后者是大家都嘗試走過的路,并且大多數(shù)都失敗了。因此作者為了提出一種合理的生存目標(biāo),即為了活著而活著,要在活著的每個(gè)當(dāng)下,活著努力、或者享受,做該做的事。而不是將期望寄放在別的地方,這樣就不會(huì)導(dǎo)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悲觀絕望。
2.就作者創(chuàng)作的動(dòng)機(jī)和題材來看,余華更適合做一名哲學(xué)家,而不是文學(xué)家。文學(xué)家要差兄做的是人文關(guān)懷,而不是解決更加深遠(yuǎn)、玄妙的理論問題。
3.“活著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這是人在沒租慶前有辦法的情況下的退守,誠如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有能力的人就該去追求超越生活的東西,做一些長久性的展望和思考。
余華
個(gè)人簡介
余華,浙江海鹽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來隨父母遷居海鹽縣。中學(xué)畢業(yè)后,因父母為醫(yī)生關(guān)系,余華曾當(dāng)過牙醫(yī),五年后棄醫(yī)從文,進(jìn)入縣文化館和嘉興文聯(lián),從此與創(chuàng)作結(jié)下不解之緣。余華曾在北京魯迅文學(xué)院與北師大中文系合辦的研究生班深造。余華在1984年開始發(fā)表,是中國大陸先鋒派的代表人物,并與葉兆言和蘇童等人齊名。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和日文等在國外出版。其中《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shí)入選百位批評(píng)家和文學(xué)編輯評(píng)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曾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xué)獎(jiǎng)(1998年),澳大利亞懸念敬物句子文學(xué)獎(jiǎng)數(shù)稿笑(2002年)。 著有短篇集《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世事如煙》,和長篇《活著》、《在細(xì)雨中呼喊》及《戰(zhàn)栗》。
余華自其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yuǎn)行》發(fā)表后,便接二連三的以實(shí)驗(yàn)性極強(qiáng)的作品,在文壇和讀者之間引起頗多的震撼和關(guān)注,他亦因此成為中國先鋒派的代表人物。
事實(shí)上,余華并不算是一名多產(chǎn)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長篇加在一起亦不超過80萬字。他是以精致見長,作品大多寫得真實(shí)和艱苦,純凈細(xì)密的敘述,打破日常的語言秩序,組織著一個(gè)自足的話語,并且以此為基點(diǎn),建構(gòu)起一個(gè)又一個(gè)奇異、怪誕、隱秘和殘忍的獨(dú)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實(shí)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實(sh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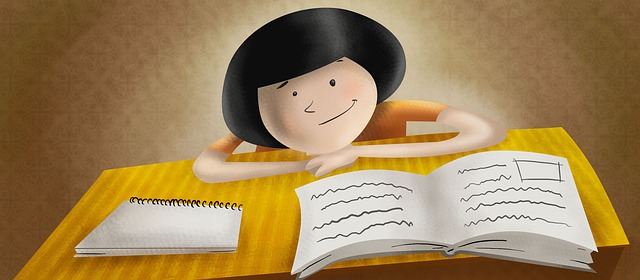
以上就是余華兩個(gè)人的歷史解析的全部內(nèi)容,平淡的敘述、平淡的語言,余華用自己的方式將一塊普普通通的豆腐翻炒出了人生的百味。火熱的年代、激烈的沖突,在通過個(gè)人經(jīng)歷得以展現(xiàn)的過程中,我們分明看到了余華那深藏著的熱烈與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