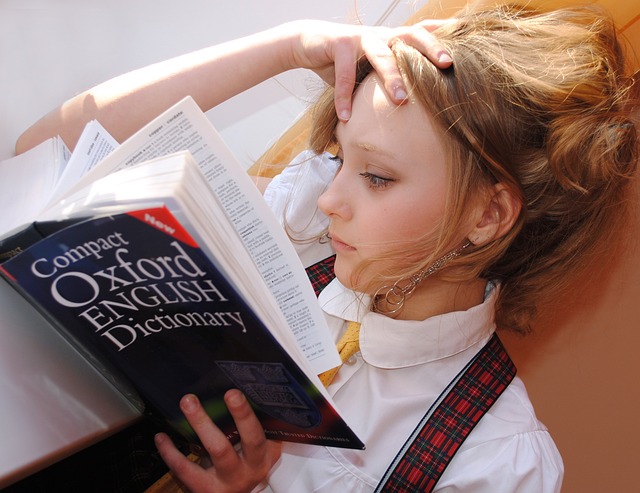目錄小學生能看懂微積分嗎 中國數學在世界的水平 數學書上最恐怖一頁 中國古代十大數學名著 中國數學和外國數學差距
數學是研究客觀事物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它不受任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強烈地顯現這一本質屬性。然而,在古代各個時期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數學的表現形式往往也不盡相同,各自呈現出自己的特征。比如中國古典數學在表現形式、思維模式、與社會實際的關系、研究的中心以及發展的歷程等許多方面與其他文化傳統,特別是古希臘數學有較大的區別。
首先是其表現形式,這里主要指數學經典的著作形式。古希臘數學常常采取抽象的公理化的形式,而中國古典數學則是以術文統率例題的形式。兩種不同的形式,代表著迥然不同的兩種風格。這兩種形式和風格同樣可以闡發數學理論的基礎。有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把中國古代數學著作籠統地概括成應用問題集的形搭槐磨式。只要仔細分析、比較一下數學著作本身,就不難發現這個結論是極不正確的。比如最重要的著作《九章算術》,它的九章中,方田、粟米、少廣、商功、盈不足、方程六章的全部及衰分、均輸、勾股三章的部分,要么先列出一個或幾個例題,然后給出十分抽象的“術”;要么先列出十分抽象的“術”,然后給出若干例題。這里的“術”都是些公式或抽象的計算程序;前者的例題只有題目及答案,后者的例題則包括題目、答案與“術”。所謂“術”就是闡述各種算法及具體應用,類似于后世的細草。《九章算術》中只有約五分之一的部分,即衰分、均輸、勾股三章的約50個題目,可以說是應用問題集的形式。由此就得出《九章算術》是一部應用問題集的結論是不恰當的,正確的提法應是術文統率例題的形式。后來的《孫子算經》等的主體應該說是應用問題集的形式,但把一些預備知識放到了卷首。宋元數學高潮中的著作,賈憲《黃帝九章算經細草》的抽象性更高于《九章算術》,其它著作由于算法更為復雜,算法的抽象性有時達不到《九章》的程度,但是也作了可貴的努力,如《數書九章》的“大衍總數術”及其核心“大衍求一術”就是同余式解法的總術;“正負開方術”用抽象的文字闡述了開四次方的方法后,又聲明“后篇效此”,說明也是普遍方法。朱世杰的兩部著作都把大量預備知識、算法放在卷首,《四元玉鑒》的卷首還載有天元術、二元術、三元術、四元術的解法范例。《測圓海鏡》更是把“圓城圖式”及后面要用到的定義、命題列入卷一的“識別雜記”。因此,總的說來,算法(術)是解應用題的關鍵,“術”自然就成為中國古代數學的核心。中國數學著作是以算法為核心,算法統率例題的形式。中國傳統文化
其次是關于數學理論的研究。古希臘數學使用演繹推理,使數學知識形成了嚴謹的公理化體系。許多學者夸大了中國古算與古希臘數學的差別,認為中國古代數學成就只是經驗的積累,沒有推理,尤其是沒有演繹推理。這是對中國古代數學缺乏起碼了解的膚淺之見。遺憾的是,這種膚淺之見被某些科學泰斗所贊同而頗為流行,甚至成為論述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出發點。誠然,中國古代數學與哲學結合得不像古希臘那么緊密,中國古代數學大家也不像古希臘數學大師那樣大多是思想界的頭面人物或思想流派的首領。一般說來,中國思想家對數學的興趣遠遜于古希臘的同仁,先秦諸子中即使數學修養最高的墨家,其數學成就也難望古希臘思想家的項背。同樣,中國數學家,就整體而言,對數學理論研究的關注,也遠不如古希臘數學家。比如,《九章算術》和許多數學著作對數學概念沒有定義,許多數學問題的表述,并不嚴謹。這就要求讀者必須站在作者的立場上,與作者共處于一個和諧的體系中,才能理解其內容,這或多或少也阻礙了數學理論的發展。硬說中明州國古代與古希臘同樣重視數學理論研究,固然是不妥的。反之,說中國古代數學沒有理論,沒有推理,也是不符史實的。《周髀算經》記載,先秦數學家陳子在教誨榮方時,指出他之所以對知斗某些數學原理不能理解,在于他“之于數未能通類”,他認為數學的“道術”,“言約而用博”,必須做到“能類以合類”。陳子大約處于《九章算術》編纂過程的初期。實際上,《九章》的編纂正是貫穿了“通類”、“類以合類”的思想。《九章算術》的作者把能用同一種數學方法解決的問題歸于一類,提出共同的、抽象的“術”,如方田術、圓田術、今有術、衰分術、返衰術、少廣術、開方術、盈不足術、均輸術、方程術、勾股術等等,又將這些術及例題按其性質或應用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九類。劉徽進一步挖掘《九章》許多方法的內在聯系,又將衰分術、均輸術、方程新術等歸結到今有術。劉徽正是通過“事類相推”,找出了各種方法的歸宿,發現數學知識是“枝條雖分而同本干”,并“發自一端”的一株大樹,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數學理論體系。賈憲總結開方法,創造開方作法本源。楊輝總結出勾股生變十三名圖,李冶探討了各種容圓關系,給出600多條公式,也都是通過歸納、類比做到通類,進而“類以合類”,進行數學的理論概括。
通過“合類”,歸納出抽象的公式之后,將這些公式應用于解某些數學問題,實際上是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過程,這里要特別談一下中國古代數學中有沒有演繹推理的問題。大家知道,數學知識的獲得,要通過類比、歸納、演繹各種推理途徑,而證明一個數學命題的正確性,則必須依靠演繹推理。中國古代數學著作正是大量使用演繹推理。以中國古代最為發達的高次方程這一分支為例,劉徽、王孝通都提出了方程的推導過程,金元數學家更創造了設未知數列方程的天元術,李冶將用天元術列方程所需要的定理、公式大都在卷一的“識別雜記”中給出。劉徽、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朱世杰等推導高次方程的過程都是依靠演繹推理的,因而是正確的。至于劉徽用極限思想和無窮小分割對圓面積公式的證明,對錐體體積公式的證明;用出入相補原理對解勾股形諸公式的證明,對大量面積、體積公式的證明,對開方術的證明;利用齊同原理對方程術、盈不足術及許多算法的證明,都是演繹推理的典范。只要不帶偏見,都會認識到劉徽在拓展數學知識時以歸納、類比為主,而在論證《九章算術》的公式、算法的正確性時,在批駁《九章算術》的某些錯誤時,則以演繹推理為主,從而把他自己掌握的數學知識建立在可靠的理論基礎之上。
說數學研究與思想界結合得不密切,是就整體而言的,并不是說每個數學家都如此,比如劉徽就例外。他深受魏晉辯難之風的影響,他對《九章算術》“析理以辭,解體用圖”,“析理”正是辯難之風的要件,劉徽析理的原則、析理的方法都是與當時辯難之風合拍的。當然,即使是劉徽對許多數學概念的探討還沒達到古希臘那么深入的地步。比如,劉徽將無窮小分割引入數學證明是前無古人的貢獻,卻從未考慮過潛無窮小與實無窮小的區別。不過,這未必是壞事。古希臘數學家無法圓滿解決潛無限與實無限的問題,不得不把無窮小概念排除在數學研究之外,因此,他們在證明數學命題時,從未使用過極限思想和無窮小分割。劉徽則不然,他認為圓內接正多邊形邊數無限增多,最后必定“與圓周合體”,因此可以對與圓周合體的正多邊形進行無窮小分割并求其面積之和;他認為對陽馬與鱉臑組成的塹堵進行無窮分割,可以達到“微則無形”的地步;劉徽在極限思想的運用上遠遠超過了古希臘的同類思想,達到了文藝復興前世界數學界的最高峰。古希臘數學家認為正方形的對角線與其邊長沒有公度,即與1沒有公度,導致數學史上的第一次危機,使古希臘數學轉向,把計算排除在數學之外,只注重空間形式的研究,因而在無理數面前束手無策。而劉徽、祖沖之等則不然,他們對“開之不盡”的“不可開”的數,敢于繼續開方,“求其微數”,以十進分數無限逼近無理根的近似值。沒有陷入哲學的爭論,從數學計算的實際出發,使中國數學家能夠繞過曾導致希臘數學改變航向或裹足不前的暗礁,在數學理論和實踐上達到古希臘數學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
長于計算,以算法為中心,是中國古代數學的顯著特點。古希臘數學只考慮數和形的性質,而不考慮具體數值。比如,他們很早就懂得,任何一個圓的周長與直徑之比是個常數,但這個常數的數值,幾百年無人問津,直到阿基米德才求出其值的范圍。相反,中國古典數學幾乎不研究離開數量關系的圖形的性質,而通過切實可行的方法把實際問題化為一類數學模型,然后用一套程序化即機械化的算法求解。算經中的“術”全是計算公式與計算程序,或應用這些公式、程序的細草,所有的問題都要算出具體數值作為答案,即使幾何問題,也要算出有關因素的長度、面積、體積。這就是幾何方法與算法相結合,或幾何問題的算法化。劉徽說:“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九章算術注·序》),清楚地表達了中國古算形、數結合的特點。《九章算術》的開方術、方程術、盈不足術、衰分術、均輸術,劉徽計算圓周率的割圓術、計算弧田面積近似值的方法,賈憲求賈憲三角各廉的增乘方法,賈憲開創而秦九韶使之完備的求高次方程正根的正負開方術,秦九韶的同余式解法,朱世杰的四元術,等等,都有相當復雜的計算程序。數學運算的程序化使復雜的計算問題易于掌握,即使不懂其數學原理,也可掌握其程序,于是產生了程序的輔助用表“立成”。上述這些程序都具有完全確定性、對一整類問題適用性及有效性等現代算法的三個特點。許多程序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搬到現代電子計算機上實現。
先進的記數制度,強烈的位置值制是促成中國算法理論充分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最早發明了十進位置值制記數法,這種記數法十分有利于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及分數、小數的表示。加之漢語中數字都是單音節,便于編成口訣,促成籌算乘除捷算法向口訣的轉化。而籌算的使用使分離系數表示法成為順理成章。線性方程組的分離系數表示法、開方式的記法、天元多項式、四元式的記法,實際上也是一種位置值制。未知數的冪次完全由其在表達式中的位置決定,而不必寫出未知數本身,如開方式中,自上而下依次是“商”、“實”(常數項)、“方”(一次項)、“一廉”、“二廉”(二、三次項系數)……隅(最高次項系數)。天元式也是如此,只是因為運算中有正冪也有負冪,才需要在常數項旁標一“太”字,或在一次項旁標一“元”字,未知數冪次完全由與“太”或“元”的相對位置決定。這種表示法特別便于開方或加減乘除運算,尤其是用天元的冪次乘(或除),只要上下移動“太”或“元”字的位置即可。
數學理論密切聯系實際,是中國古代數學的又一顯著特征。不能把古算經的所有題目都看成日常生產生活的應用題,有些題目只是為了說明算法的例題,《九章算術》和《測圓海鏡》中都有此類題目。但是,中國古算確實是以應用為目的的,這是與古希臘數學的顯著區別之一。后者公開申明不以實際應用為目的,而是看成純理念的精神活動,歐幾里得幾乎抹去了《幾何原本》的實際來源的所有蛛絲馬跡。而中國數學家卻從不諱言研究數學的功利主義目的。自《漢書·律歷志》到劉徽、秦九韶,都把數學的作用概括為“通神明”、“類萬物”兩個方面。這里神明的意義既可作神秘主義來理解,也可以看作說明物質世界的變化性質的范疇,或二者兼而有之。《九章算術》劉徽為其注沒有任何神秘主義的成份,對通神明的作用也沒作任何闡發,劉徽倒是明確指出了《九章算術》各章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應用范圍: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勾股以御高深廣遠,顯然是“類萬物”方面。秦九韶把“通神明”看作數學作用之大者,并且其理解是神秘主義與世界變化的性質二者兼而有之的,而把類萬物、經世務看成數學作用之小者。盡管他表示要將數學“進之于道”,但他的數學研究實踐使他感到對于大者仍“膚末于見”,而注重于小者,認識到“數術之傳,以實為體”,因此“設為問答以擬于用”。他的《數書九章》除第一問外,大都是實際生活、生產及各種工程的應用題,反映南宋經濟活動之翔實遠勝于《九章算術》等著作對當時現實經濟活動的反映。總之,中國數學密切聯系實際,并在實際應用中得到發展。也許正因為有這個長處,中國數學從《九章算術》到宋元高潮,基本上堅持了唯物主義傳統,未受到數字神秘主義的影響。明朝著作有一些神秘主義的東西,具有穿靴戴帽的性質,但仍不能改變以實際應用為目的這一總的特征。
統治者對數學的態度造成了中國與希臘數學不同的發展特點。古希臘統治者非常重視數學,造成希臘數學有很強的連續性、繼承性。而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除個別者外,大都不重視數學。秦始皇統一中國,較為重視數學的墨家遭到鎮壓,漢朝以后獨尊儒術,儒法合流,讀經學禮,崇尚文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由于數學對國計民生的重大作用,統治階級又不得不承認“算術亦六藝要事”(《顏氏家訓·雜藝》),但卻主張“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同上)。數學一直被視為“九九賤技”。劉徽哀嘆“當今好之者寡”,(《九章算術注·序》)秦九韶說“后世學者鄙之不講”,(《數書九章序》)李冶以大儒研究數學,自謂“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測圓海鏡序》)劉徽所處之魏晉,秦、李所處之宋元,都是中國數學興盛時期,尚且如此,何論其他!二十四史,林林總總,列入無數帝王將相,以及文學家、思想家,甚至烈女節婦,卻沒有為一個數學家立傳,祖沖之、李冶有傳,卻是以文學家、名臣的身份入傳的。社會的需要,以及世代數學家不計憫笑,刻苦鉆研,自漢迄元,使中國數學登上了世界數壇的一個又一個高峰,然而中國數學的發展常常大起大落,艱難地前進。更使人覺得奇怪的是,高潮往往出現在戰亂時期,如戰國時期《九章算術》主要成就的奠基,魏晉南北朝數學理論的建立,宋遼金元籌算數學的高潮;相反,低谷往往出現在大一統的太平盛世,如唐、明兩代,不僅數學建樹甚少,甚至到了大數學家看不懂前代成果的可笑地步!這當然絲毫不意味著戰亂、分裂比安定、統一更有利于數學的發展,而是因為戰亂時期,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往往受到沖擊,社會思潮較為活躍,思想比較解放。同時由于戰亂,讀經入仕的道路被堵,知識分子稍稍能按自己的興趣和社會的需求發揮自己的才智,所蘊藏的數學才能也得到較充分展示,致使處于夾縫中的數學研究狀況反而比大一統的太平盛世更好一些罷了。
中國的數學家是陳景潤。
陳景潤,福建福州人,當運逗代數學家,被公認為對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做出過重大貢獻。
陳景潤早年就讀于福建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廈門大學,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1955年,他又被調回廈門大學數學系任助教。1957年,他拆悄仿受到華羅庚的重視,被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
1977年,華羅庚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后又當選中科院物理學數學部委員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6年,陳景潤在北京去世。
人物事件
他有著超人的勤奮和頑強的毅力,多年來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數學研究,廢寢忘食,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在遭受疾病折磨時,他都沒有停止過自己的追求,為數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的事跡和拼搏獻身的精神在全國各地廣為傳頌,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目中傳奇式的人物和學習楷模。在旅纖福建省三明市檔案館里,珍藏著三明一中(前身為三元縣立初級中學)全宗檔案,歷經歲月風塵,它們仿佛在述說著歷史的滄桑。
翻開第一號目錄第三卷,透過其中幾頁薄薄的毛邊紙,有些字跡雖然有些褪色,但我們可以看到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在三明留下的足跡:1945年2月升入三元縣立初級中學,全班學生共有18名,修業年限定為三年;1947年1月,陳景潤上完初二、上初三之前隨父親離開三元縣返回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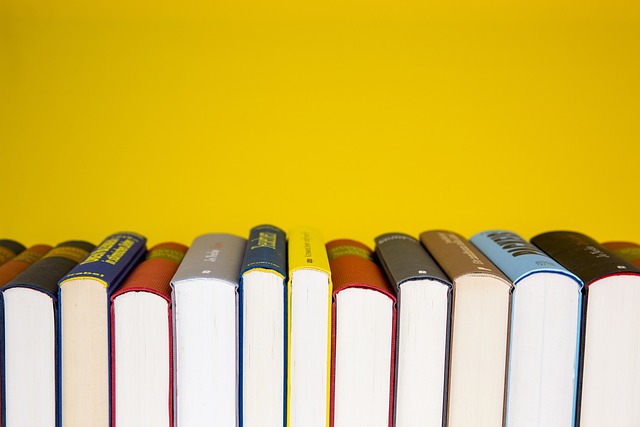
盡管不情愿,但是,我們必須艱難地承認,我們的數學能力距離世界頂尖水平還有非常巨大的鴻溝。我們可以來一起簡單審視一下:
第一,中國的數學解題能力很強,但解決問題能力不強。
誠然,我們有全世界最厲害的計算能力,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能夠通過記憶和反復訓練習得的能力已經不那么重要。
解題能力VS解決問題能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解決問題重在發現未知問題,提出模型,解決隨機不確定的任務;而解題只是學會已知基礎數學知識點,所以解題是個沒有創造性的工作,那些題解與不解、解得快與慢,已知答案千百年來早已經等在那里。
競賽的風向標也越來越趨向解決問題能力的考核,因此中國今年羅馬尼亞大師賽全軍覆沒也就不顯意外了。近幾年奧林匹克國際競賽李螞的第一也都是美國隊。
第二,中國的數學教育體系過于僵化,不注重創造性數學思維的培基巖養。
數學能力重要的是思維能力、決策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我們當前的填鴨式教育正好背道而馳。有人說中國只重視基礎教育,不重視高等教育,但其實,從基礎教育開始,我們的方向就是錯的。我們從小到大的訓練都是如何把題做準確、做快,缺少啟發性、創造性教學。
這種體制下培養出的學生缺少獨立思考的訓練,只會按照老師的指定路線向前。因此,中國想要在數學領域領先、處于領導地位,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
曾有一個留學劍橋的學生,悔恨地和媽媽提起:媽媽,我現在才知道我最熱愛的是數學啊!我和學習數學的同學聊天,才發現數學真的很美!但我過去所受到的枯燥訓練扼殺了我對數學的興趣,讓我討厭數學,現在我才發現這是多么錯誤的!
也許我們也可以有很多很偉大的數學家,但都被這樣的原因耽誤了。
第三,只聽說中國的數學家到美國等國家留學,但鮮有聽說國外數學家到中國留學。
中國有很多著名的華人數學家,華羅庚、陳景潤、蘇步青、陳省身、丘成桐、張益唐等,但只有陳景潤沒有留過學。國外數學家來中國學習卻無異于天方夜譚。
中國兩千年來都沒有出現過類似高斯、黎曼等這樣千年一遇的數學家。中國教授和科研工作者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院士”,獲得學術和行政權益。真正醉心純粹學術研究的老師少之又少,普遍以應用為主,基礎為輔。但中國的應用數學還未達到世界水平,基礎數學就更不用說了。
第四,中國缺少對數學真心熱愛的學生,往往抱著功利的態度。
中國學生對數學往往缺少真心熱愛,缺乏激情,缺少好奇心,以及揭秘數學奧秘的行動力,更多是將數學視為獲取體面工作、舒適生活的手段,曾有國外教授,她最得意、最有天賦的學生畢業后告訴她要放棄學術,投身投行,因為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哪鋒埋。她氣憤表示從此再不收中國學生。
第五,即便華為引領了5G標準,但發揮核心作用的也是以國外科學家為主。
5G的緣起是因為一位土耳其畢爾肯大學(bilkent)教授Erdal Arikan在2008年發表的一篇關于極化碼(polar code)的論文。華為的主要科學家也主要來自俄羅斯、以色列等西方國家,我們不能被眼前的成果掩蓋自身的問題。我們的數學發展一直踩著國外的腳印,缺少自主發明,更不用談引領數學科學走向。
數學是科學的起點和終點,其方法貫穿科學研究的始終,并起著關鍵作用。不管人工智能、大數據、無線電……幾乎所有的技術底層都會指向數學,相關博士研究也都會回歸數學。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說,中國數學經過八十年的努力,也還沒有達到日本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的盛況。更遑論美國。
但我們也不是全然沒有機會:中美貿易戰是一個讓中國重視數學教育的契機,每年有越來越多的留學學者歸國,而美國方面也正在面臨行政干預科研、科學家倚老賣老等問題,中國數學把握機遇,還是很有希望縮短差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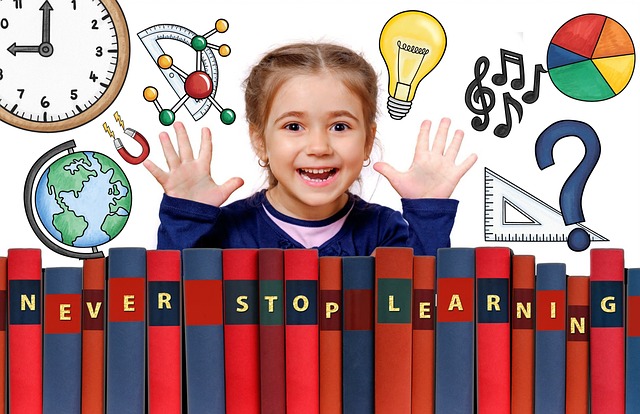
翻開任何一部中國數學發展史,都不難發現,華夏祖先們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奮斗的汗水。中國數學起源于上古至西漢末期,中國數學的全盛時期是隋中葉至元后期。接下來在元后期至清中期,中國數學的發展緩慢。就在中國數學發展緩慢的時候,西方數學已大跨步超前,于是在中國數學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個中西數學發展的合流期,這一時期約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間。近代數學的開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這一時期。盡管中國目前在世界數學的賽場上已處落后地位,然而,路遙識馬力羨虛渣,今后鹿死誰手,仍然未可知
數學的意義數學發展史數學文化數學史中國數學史中國數學發展史簡介中國數學發展史數學發展
古希譽拿臘學者畢達哥拉斯(約公元約前580~約前500年)有這樣一句名言:"凡物皆數"。的確,一個沒有數的世界不堪設想。
今天,人們對從1數到10這樣的小事會不屑一顧,然而上萬年以前,這事可讓人們煞費苦心。在7000年以前,他們甚至連2以上的數字還數不上來,如果要問他們所捕的4只野獸是多少,他們會回答:"很多只"。如果當時要有人能數到10,那一定會被認為是杰出的天才了。后來人們慢慢地會把數字和雙手聯系在一起。每只手各拿一件東西,就是2。數到3時又被難住了,于是把第3件東西放在腳邊,"難題"才得到解決。
就這樣,在逐步摸索中,華夏民族的祖先從混混沌沌的世界中走出來了。
先是結繩記數,然后又發展到"書契",五六千年前就會寫1~30的數字,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祖先們不但能寫3000以上的數學,還有了加法和乘法的意識。在金文周<※鼎>中有這樣一段話:"東宮乃曰:償※禾十秭,遺十秭為廾秭,來歲弗償,則付秭。"這段話包含著一個利滾利的問題。說的是,如果借了10捆粟子,晚點還,就從借時的10捆變成20捆。如果隔年才還,就得從借時的10捆漲到40捆。用數學式子表達即:
10+10=20
20×2=40
除了在記數和算法上有了較大的進步外,華夏民族的祖先還開始把一些數字知識記載在書上。春秋時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修改過的古典書籍之一<周易>中,就出現了八卦。這神奇的八卦至今在中國和外國仍然是人們努力研究和對象,它在數學、天文、物理等多方面都發揮著不可低估和作用。
到了戰國時期,數學知識已遠遠超出了會數1~3000的水平。這一階段他們在算術、幾何,甚至在現代應用數學的領域,都開始了耕耘播種。算術領域,四則運算在這一時期內得到了確立,乘法中訣已經在<管子>、<荀子>、<周逸書>等著作中零散出現,分數計兄悄算也開始被應用于種植土地、分配糧食等方面。幾何領域,出現了勾股定理。代數領域,出現了負數概念的萌芽。最令后人驚異的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對策論"的萌芽,對策論是現代應用數學領域的問題。它是運籌學的一個分支,主要是用數學方法來研究有利害沖突的雙方,在競爭性的活動中,是否存自己制勝對方的最優策略,以及如何找出這些策略等問題。這一數學分支是在本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后,才作為一門學科形成的,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公元前360~前330年)就提出過"斗馬術"問題,而這一問題的內容,正反映了對策論中爭取總體最優的數學思想。"斗馬術"問題說的是,齊威王要和大將田忌賽馬,他們每人各有上、中、下等馬各1匹,田忌那3匹馬比起齊威王的來,都要略遜一籌,如果用同等級的對應較量法,田忌必輸無疑,田忌為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孫臏從旁點撥,田忌用了孫臏的辦法,以2:1取勝齊威王。
中國的數學家是:
1、吳文俊(1919年5月12日-2017年5月7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嘉興,畢業咐埋于斯特拉斯堡大學,著名數學家,中國數學機械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
2、胡明復(1891.5.20~1927.6.12),原名孔孫,后改名為達,字明復,中國以攻讀數學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參與創建了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和最早的綜合性科學雜志——《科學》。
3、陳景潤(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人,無黨派人士。生前系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數學家,畢業于廈門大學,當代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最美奮斗者”。
4、華羅庚,出生于江蘇常州金壇區,祖籍江蘇丹陽,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羅庚主要從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守函數論、多復變函數論、偏微分方程、高維數值積分等領域的研究。
5、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郡遒縣(今河北省淶水縣)人,南北朝時期杰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答派。出身范陽祖氏。一生鉆研自然科學,其主要貢獻在數學、天文歷法和機械制造三方清簡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