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怎樣能夠聽懂音樂 如果想真正地感受和理解音樂 一個音樂獲得張力的最重要因素 對真正了解音樂 純音樂怎么聽懂

音樂是靠自己的心去感受的,可以多聽一些比較著名的鋼琴曲洞拿,不能執著于一種類型納明搭的,可以多去嘗試不同的風格槐伏。每個風格都有相對的音樂大師,都可以試試去聽聽看,我雖然沒有很懂音樂,當是知道勇于嘗試各種音樂類型總是好的。
話說音樂音樂在描繪什么的問題我更傾向用《肖申克的救贖》里那句臺詞來回答:盡管我完全不清楚那女人在唱什么,但是我希望她是在用世界上最美的聲音唱著這個世界上最美的東西。音樂愛好者直接從感官上得到的音樂形象比學了一系列音樂知識后再去分析的更為直接。現在經過一系列音樂欣賞的訓練后,我發現自己再也回不去那種直接欣賞音樂的程度了。兩種欣賞可以說各有好處,前者更為豐富,想象力和創造力能被極大的調動起來,更多角度的完成音樂作品的再創造過程;后者經過訓練后,聆聽音樂就變成從音樂的各種組成要素來分析,旋律、音色音區、節奏節拍、調式、和聲、織體、曲式等等,其欣賞可以說是艱苦的。不過最后能夠從音樂中獲得的資訊無疑是最豐富,也最深刻的。當然不是選了一種另外一種就做不到,只是本人較水,還沒能跳出去而已。回到樓主的題目,其實回答很簡單,耶魯大學有一個公開課叫《聆聽音樂》,雖然很長,但絕對是一般音樂愛好者的進階寶典,Craig Wright教授就是從這些音樂的組成要素來講如何聽西方古典音樂的,這課我個人覺得很有必要看,看了就有樓上的那種進入另一個世界的感覺了
麻煩采納,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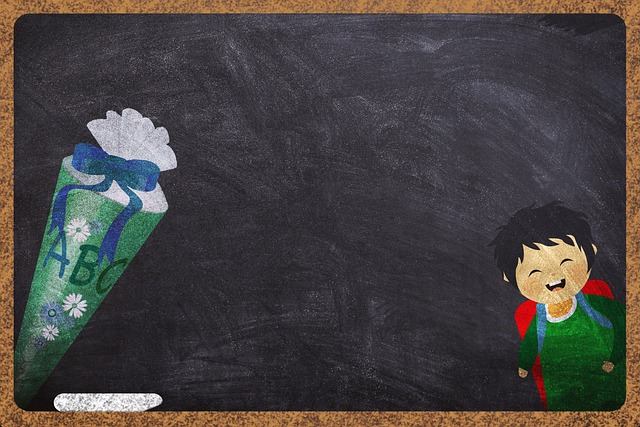
廣義的講,音樂就是任何一種藝術的、令人愉快的、審慎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來的聲音。所謂的音樂的定義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議,但通常可以解釋為一系列對于有聲、無聲具有時間性的組織,并含有不同音階的節奏、旋律及和聲。
音樂可以通過幾種途徑來體驗,最傳統的一種是到現場聽音樂家的表演。現場音樂也能夠由無線電和電視來播放,這種方式接近于聽錄音帶或看音樂錄像。有些時候現場表演也會混合一些事先做好的錄音,如DJ用唱片做出的摩擦聲。當然,也可以制作自己的音樂,通過歌唱,玩樂器或不太嚴密的作曲。
甚至耳聾的人也能夠通過感覺自己身體的震動來體驗音樂,最著名聾音樂家的例子便是貝多芬,其絕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喪失聽力后創作的。
人們想學習音樂的時候會去上音樂課。音樂學是一個歷史的科學的研究音樂的廣闊領域,其中包括音樂理論和音樂史。
音樂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極大量的音樂流派已經發生變化。人種音樂學作為人類學的一個分支是專門研究這些流派起源及發展的學科。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說法很多。筆者認為音樂是一種聲音藝術而非視覺或其它什么感覺的藝術。把樂音(有時也適當使用噪音)按一定的規律組織起來,使人聽之產生美感,這種藝術就叫音樂。
聲音四要素是:音強、音高、音色和波形包絡。現將它們的含義分述如下:
1.音強
音強就是人們在聽聞時感到的響度,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聲音的強弱或大、小,重,輕。它是人耳對聲音穩弱的主觀評價尺度之一。其客觀評價尺度——也即物理量的測量,是聲波的振幅。音強與振幅并不完全一致或成正比,在聲頻范圍的低頻段相差很大,高頻段也有相當的差別。
聲頻范圍也就是人們可以聽到的聲振動頻率范國,為20赫到20千赫。20赫以下稱為次聲波,20千赫以上稱為超聲波。在聲頻頻率范圍內,人耳對中頻段1~3千赫的聲音最為靈敏,對高、低頻段的聲音,特別是低頻段的聲音則比較遲鈍。人耳還有一種特征,對很強的聲音,感覺其響度與頻率的關系不大,或者說同振幅的各頻率的聲音,聽起來響度差不多.但對低聲級信號(即很輕的聲音),感覺到它的響度與頻率關系甚大:對于同樣振幅的聲音,低、高頻段的聲音聽起來響度比中頻段的輕。聲音振幅愈小,雞種現象就愈嚴重。對1千赫的聲音信號,人耳所能感覺到的最低聲壓為2X10(負4次方)微巴。微巴是聲壓的單位,,它相當于在1平方厘米面積上具有1達因壓力。電聲工作者把這一聲壓稱為聲壓級的0分貝,通常寫為O分貝SPL(SPL是聲壓級的縮寫),正如把0。775伏定為在6OO歐電路中的0分貝一樣。不用聲壓而用以對數表示的“聲壓級”來表示聲音振幅的大小,有明顯的好處。這是因為人耳能聽聞的聲壓范圍很大,可由2X10(負4次方)微巴到2XlO(負四次方)微巴,相差一千萬(1C)倍。對如此大范圍的變化,計算很不方便,用聲壓級表達就比用聲壓方便多了。另外由于人耳對響度的感覺是非線性的,用對數來計量更接近于人耳的主觀特性。當聲壓級達120分貝SPL時,人耳將感到痛楚,無法忍受,因此,人聽聞的動態范國由0~120分貝SPL,在音樂廳中聽樂隊演奏,音樂的自然動態范圍是多少呢?對大型交響音樂,最響的音樂片段可達115分貝SPL,最弱的音樂片段約為25分貝SPL,因而動態范圍可達90分貝。當然,這是很少有的情況。通常交響音樂的動態范圍約為50~80分貝,中、小型音樂的動態范國約在40分貝左右,語言的動態范圍約在30分貝左右。
因此,要求家用放音設備能夠盡可能地再現:
1〕上述音樂或語言的自然聲級動態范圍。
2〕音樂或語言的自然聲壓級。對于家庭內常用的放音音量,平均聲壓級對音樂來說約為86分貝SPL,對語言則約為70分貝SPL左右。
2.音高音高或稱音調,是人耳對聲音調子高低的主觀評價尺度。它的客觀評價尺度是聲波的頻率。和音強與振幅的關系不一樣,音高與頻率基本上是一致的。當兩個聲音信號的頻率相差一倍時,也即f2=2f1時,則稱f2比f1高一個倍頻程。音樂中的1(do)與i,正好相差一個倍頻程,在音樂學中也稱相差一個八度音。在一個八度音內,有12個半音。以1—i八音區為例, 12個半音是:1—#1、#1—2、2—#2、#2—3、3—4、4—#4,#—5、5一#5、#5—6、6—#6、#6—7、7—i。請注意,這12個音階的分度基本上是以對數關系來劃分的。
各種不同的樂器,當演奏同樣的頻率的音符時,人們感覺它們的音高相同,這里指的演奏的聲音具有同樣的基頻。但樂器每發一個音,這個音除了具有基頻fo,以外,還有與fo成正整數倍關系的諧波。前面說過,每個音的音高感覺由fo決定,而每種樂器的不同各次諧波成分,則決定樂器特有的音色。那么,音樂的自然基頻范圍是多少呢?樂器中,基音頻串范圍最寬的是鋼琴,由27.5~4136赫。管弦樂、交響樂的基音范圍是30~60OO赫。我國民族樂器的基音范圍則為50~4500赫。 順便介紹一下,現代電聲學研究說明,樂音的自然頻率范圍已經超出20~20000赫可聞聲頻串范圍之外,例如某些非洲鼓的基音在次聲頻頻段,而某些中國木管的諧波(泛音)可達25千赫之高。次聲信號雖不能為人耳所感聞,但可為人的皮膚所感知。另外,語言畫基頻在150~3500赫范圍內。
3.音色
人們除對響度、音高有明顯的都別力外,還能準確地判斷聲音的“色調”。單簧管、圓號雖然演奏同一音高(基頻)的音符,但人們能夠明確分辨出哪個是單管管,哪個是圓號,而不會混淆。這是由于它們的音色、波形包絡不同。音色決定于樂音的泛音(諧波)頻譜,也可以說是樂音的波形所確定的。因為樂音的波形(可由電子示波器上看到〉絕大多數都不是簡單的正弦波,而是一種復雜的波。分析表明這種復雜的波形,可以分解為一系列的正弦波,這些正弦波中有基頻f0,還有與f0成整數倍關系的諧波:f1、f2、f3、f4,它們的振幅有特定的比例。這種比例,賦予每種樂器以特有的“色彩”一——音色。如果沒有諧波成分,單純的基音正弦信號是毫無音樂感的。因此,樂器樂音的頻率范圍,決非只是基頻的頻率范圍,應把樂器樂音的各次諧波都包括在內,甚至很高次數的泛音,對樂器音色影響仍很大。高保真放聲要十分注意讓各次泛音都能重放出來,這就使重放頻串范圍至少達15000赫,要求潮的應達20千赫或更高。另外,語言的泛音可達7~8千赫。
4.波形包絡
樂音的波形包絡指樂音演奏(彈、吹、拉,撥)每一音符時,單個樂音振幅起始和結束的瞬態,也就是波形的包絡。有些樂器,在彈、吹、拉、撥的開始一瞬間,振幅馬上達到最大值,然后振幅逐步衰減,有的樂器則相反,在開始的瞬間振奮較小,然后逐漸加大,再逐漸衰減。這些波形包絡變化也影響樂器的音色。 顯然重放設備也要求有較好的瞬態跟隨能力,不然就會引起樂音自然包絡的畸變。
近古音樂——兩千年的理論探索與十二平均律的誕生
在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遺產中,有一門科學,自公元前7世紀起便有人開始探究。其后2600余年,綿延不絕,一直持續到今天。它就是一度被學術界稱為“絕學”的“律學”。
律學,即研究樂音體系中音高體制及交互的數理邏輯關系的科學。它是音樂聲學(音響學)、數學和音樂學互相滲透的一種交叉學科。在有關音高體制的研究與應用中,律學規律幾乎無處不在。例如:旋律音程的結構與音準;調式與和聲理論中的和諧原則;多聲部縱向結合時的各種音程關系;旋宮轉調;樂器制造及調律中的音準與音位的確定;重唱重奏、合唱合奏中的音準調節,都與律學有直接關系。因此,一部“二十四史”,除了“樂志”,每朝都立“律志”、“律書”及“律歷志”之類的篇章。
“律學”遺產之豐富,它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便可想而知了。
中國樂律史上最早產生完備的律學理論,稱為“三分損益律”,它大約出現千春秋中期。《管子·地員篇》、《呂氏春秋·音律篇》分別記述了它的基本法則:以一條弦長為基數,將其均分成三段,舍一取二,“三分損一”,便發出第一個上五4度音;如果將均分的三段再加一段,“三分益一”,便發出第一個下4度音,用這種方法繼續推算下去,可得12個音,稱“十二律”,每律有固定的律名,即:(以下兩行要豎著讀)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鐘 呂 簇 鐘 冼 呂 賓 鐘 則 呂 射 鐘
因為這種“生律法”是一步步推算5度音,所以又叫“五度相生律”。管子稍晚,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前580一前501)也以同樣的方法推算出“十二律”。
“三分損益”雖然推演出“十二律”,但計算到最后一律時卻不能循環復生,哪它是一種不平均的“十二律”,各律之間含有大、小半音之別。因此,為了尋求一種可以自由地旋宮轉調的平均律制,就成了兩千多年來樂律學家們孜孜以求的理想。
漢朝著名律學家京房(前77—前37)沿著五度相生的方法連讀推算下去,至第53“色育”律時,己基本還原到出發偉“黃鐘”(歐洲在16世紀時也出現過53平均律)。
他最后算到60律,后世稱“京房律”。表面上看,京房推算60律的繁復律制,與簡練的十二平均律理想南轅北轍,但如果拋開它神秘主義的外衣,他在運算過程中得到的許多律高,都可以在曾侯乙編鐘所體現的“鐘律”上予以印證。南朝的錢樂之、沈重在京房60律的基礎上繼續按“二分損益法”推演生律,直至更為周密的360律。他們把還生黃鐘本律的音差數縮小到最少程度,從而為從其中選擇十二平均律各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同時沿此途求解十二平均律的探索也步入“山窮水盡”的困境。
不無巧合的是,與錢、沈同時代的樂律學家何承天(370一447)大膽提出一種“新律”。他的作法是把第十二律不能還原所剩的誤差數,分作十二份,每律增補一份。
十二次相生后,正好回歸黃鐘律。這可以說是天才的十二平均律構想,何承天在當時幾乎就要叩開這一高深莫測的律制的大門了,可惜他不是按頻率比計算,而是依弦長計算,難題再度擱淺。隋代劉焯(581一618)擺脫“三分損益律”的羈絆,以振動體長度桐鄰律之間的差數相同,推算出“十二長度等差律”。王樸(905一959)于959年又提出一種“新律”,以倍半關系的八度音程硬性調整各律。他清楚地認識到,解決不平均律的矛盾只能在12律范圍內進行,但他的基本方法還是在“三分損益法”上修修補補。
經歷樂如此漫長的探索和徘徊,至明朝中時,皇族朱載堉(1536一1611)終于成為登上律學的寶塔頂摘取“十二平均律”明珠的第一人。他以珠算開方的辦法,求得律制上的等比數列,第一次解決樂十二律內自由旋宮轉調的千古難題,實現了千余年來無數律學家夢寐以求的理想。他的“新法密率”已成為人類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作為一位藝術史上的巨人,朱傤堉在科學、文化特別是傳統樂律學理論方面都有建樹。他積終生而著的《樂律全書》囊括了音樂藝術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中國封建社會日趨衰微。朱傤堉發明的“十二平均律”。終于未能付諸實踐,被藏在一函書籍之中而束之高閣,成為反映封建帝國扼殺天才的一個悲劇性的側影。
上古音樂——發展史(一)
先秦典籍《呂氏春秋》里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至何時,史無確載,但不斷發現的音樂文物,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它的“由來”之遠。
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安陽殷墟“商代虎紋大石磐”出土,證明中國樂器已有3000余年的歷史;五十年代中,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一音孔陶塤”,樂器曳一下子上溯到6700余年前;七十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又發現大批7000多年前的“骨哨”和一件“陶塤”……中國音樂確實像一條歷史的長河,這條河曲折婉蜒、多姿多彩,永不止息;這條河由涓涓細流匯成滔滔大江。近些年,河南舞陽賈湖村的一次考古發掘使它再向更古老的年代延伸……
中國音樂的歷史,古代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盡管關于黃帝的傳說夾雜著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內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說黃帝時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來的創造歸功于黃帝的說法,與現代科學考古發現不合。)要把黃帝作為中國音樂的源頭,也嫌太晚了:現代考古發現已把中國音樂的歷史,從黃帝時代大大向前推進棗其歷史遠比黃帝時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新石器遺址發掘出了隨葬的至少16支骨笛,據碳14測定,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這些骨笛用鶴類尺骨制成,大多鉆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還遺留著鉆孔前刻劃的等分標記,個別音孔旁邊另鉆一小孔,應是調整音高用的。這些情況起碼說明,那時人們已對音高的準確有一定要求,對音高與管長的關系也已具備初步認識。經音樂工作者對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測音可知,號稱以五聲音階為主的中國,其實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備了有著穩定結構,超出五聲的音階形態了。(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音樂后來以五聲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謂“音階發育不完善”,而是一種歷史的、審美的選擇結果。)這也證明當時的音樂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在這之前,中國音樂一定還存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以千年還是以萬年計,現在難以猜測。
除骨笛外,新石器時期的樂器,還發現有骨哨、塤、陶鐘、磬、鼓等。這些樂器分布于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時間跨度也很大,說明它們是中國原始時期的主要樂器。其中鐘、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至于塤和哨,還有與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稱為“籌”)的樂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間。
塤是一種很有特點的樂器,用土燒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種變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頭,中空,頂端開一吹孔,胸腹部開一個或數個指孔。塤是除骨笛之外,已發現的原始時代樂器中唯一能確定地發一個以上樂音的樂器,原始時期的塤只有1-3個音孔,只能吹出2-4個音,(這很可能與在不大的蛋形的塤上開孔,比在管狀的笛上開孔要難以計算有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音階發展的進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國音階的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關系;當今有學者指出,那就是從只能發兩個音的一音孔塤起便一再被強調的小三度音程。這一觀點對于認識中國音階的發展,音階音之間的律學關系,乃至中國的七聲音階仍以五聲為骨干現象的內在機理,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原始時期的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歷史上共有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最遲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已稱這種音樂舞蹈結合的藝術形式為“樂”,甚至在音樂舞蹈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之后,“樂”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樂,一直保存著它的模糊詞義。今天“樂”已專指音樂,所以學者通稱原始時期的“樂”為“樂舞”。現存的有些原始巖畫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原始樂舞的場面,那是一種群體的歌舞活動。據后來文獻保留下的片斷“記憶”可知,原始樂舞的舉行跟祈求豐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產活動的再現成份。
原始時期,樂舞并不成其為社會分工對象,原始社會不存在專職的樂工,樂舞一般是部落社會的全社會活動。因此,原始時期的樂舞,并沒有以專門的藝術形式的面貌和身份,從社會上獨立出來。
嚴格地說,到大約公元前21世紀夏代建立以后,樂舞才真正作為一種社會分工,從社會中取得獨立。傳說夏朝初期的國君啟和最后的國君桀,都曾用大規模樂舞供自己享樂,說明終夏一代,社會已造就出一大批專職的樂舞人員,這正是樂舞作為藝術而獨立于社會的標志。
由于原始樂舞即和原始巫術、祭祀等活動結合無間的緣故,人們對樂舞乃至一些樂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產生得很早。國家產生以后,統治者便會利用和加強音樂神秘觀,以便操縱、控制樂舞,用來加強其統治。保存下來的一些音樂神話故事便是這樣的社會背景的產物。傳說分為章節的大型樂舞《九辯》、《九歌》都是夏代國君啟從天上得來的。我們從出土的戰國初年(公元前5世紀)的樂器上,還能看到啟的圖象,似乎他那時已具有司音樂之神的地位了。又傳說黃帝得到一種長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動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獸的骨頭作鼓槌,敲打起來,“聲聞五百里”,黃帝用這面鼓揚威天下。夔和雷獸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動物。那時的鼓,實際上和后世一樣,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鼉(今稱揚子鱷)皮的,因此也成了神話材料。后來,夔轉化成為主管音樂的“人”(神)。蒙鼓的夔成為主管音樂的神,應該看作是支配節奏的鼓這件樂器在樂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賈湖骨笛的出土地點,靠近傳說中夏代的夏臺,這告訴我們,夏代的活動區域,正是中國音樂高水平發展的地區。傳說中夏代樂舞明顯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剝去上述《九辯》、《九歌》是啟從天上得來的神話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現實中的《九辯》、《九歌》確實無比瑰麗優美這一點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發人們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進一步創造出神話來。
鋼琴是所有樂器中的國王,小提琴是所有樂器中的王后。鋼琴的琴鍵所帶出的感受有流利暢快之感,力道強。著名的曲子有《致愛麗絲》,《月光曲》等。小提琴的音域廣,聲音細膩,行云流水,富有感染力。著名的曲子有《梁祝》、《流浪者之歌》等。鋼琴和小提琴都適合合奏及協奏曲,可以說他們倆形影不離。
貝多芬是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家之一,他有著坎坷的人生,因此創作的曲子多是與命運抗爭的主題,帶著強烈的悲壯色彩。他一生作的交響曲并不多,只有九部,但影響深遠。
巴赫是著名的奏鳴曲作家,他的第一首曲子是在月光下的屋頂上誕生的。曲調歡暢流利,輕盈非凡。
薩拉薩特是浪漫派作家。他的曲子都積極向上,奔放豪邁。
維俄當和布魯特追求的是技術技巧,因此他們的曲子一般缺少柔美與情感,但難度高。
這就是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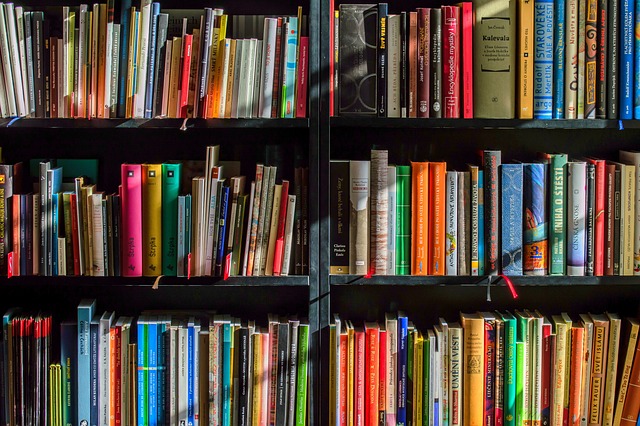
個人不同的啊~~~~~~~~~~
樓上的亂弄的,這么多,看都累死類~~~
投入地去聽,可以感受到一些的東西,就是一種懂~~
如何欣賞音樂如下:
個人拙見音樂是外界與心靈交匯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好的音樂可以打動人心,撼動心靈,使人陶醉其中。
音樂,可以用“清脆”一詞來形容,在日常我們所聽到的曲之中多為輕快型,用清脆一詞恰好與其相符合。
也可以用婉轉悠揚"來形容,以情為引而譜曲,最能打動人心,當以思情、愛情、親情為引,自然所譜寫出的曲風曲調比較婉轉悠揚。